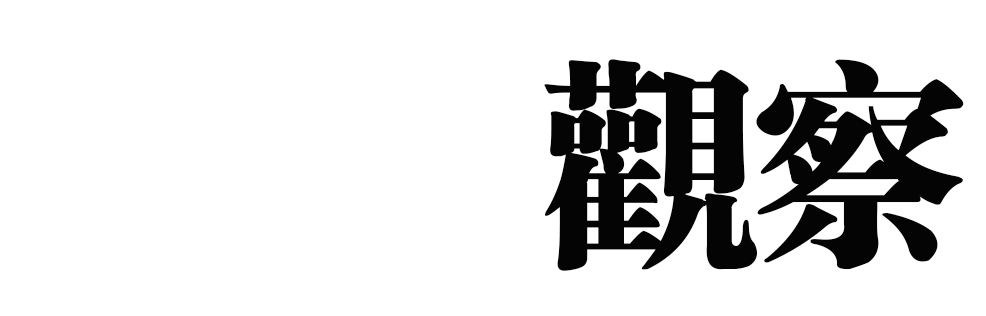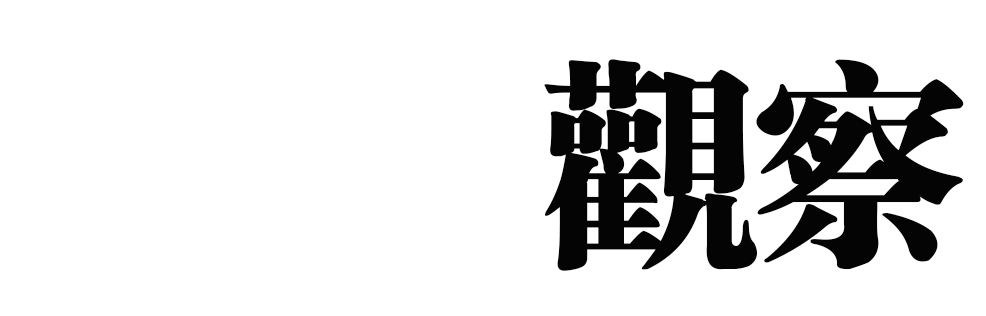三峡人物
陆佑楣:用主流眼光看待三峡工程
发布时间:2010-09-27 23:42:00
2004年7月 新京报 袁凌 湖北宜昌报道
时隔一月记者再访三峡总公司前总经理,更为充分地探讨三峡热点问题
■对话动机
6月7日,三峡蓄水一周年之际,记者专访中国三峡总公司前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发表题为《十问三峡》的访谈录,从多方面详细探讨了三峡工程受人关注和争议的话题。
报道刊出后社会反响强烈,部分网络读者发表的意见超出了本报的预料。6月16日,陆佑楣院士给本报来信,认为报道未能全面准确地表达他的意见。这封信随后在互联网上流传,再次激起各方讨论。
7月8日,三峡船闸通过国家级验收之际,记者抵达地处宜昌的中国三峡总公司,再访陆佑楣院士。
三峡工程是理性思考结果
新京报:《十问三峡》发表后,读者的反映之强烈超出了本报预料,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一些片面、偏激的言辞。我想,除了报道本身带有一定质疑性,这更证明三峡工程确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您更充分和全面地表达对相关问题的意见。
陆佑楣(以下简称陆):三峡工程不是一两天、一两个人搞出来的,是经过了几十年、近百年论证的大工程,是几代人的努力,它不是一般的工程,因此对于三峡工程,不能抓住一两个枝节问题就行了,而是要有一种主流的眼光,一定要从主流问题、主流社会来看。只抓住一两个枝节,看问题就会片面失真。
新京报:主流的眼光或者主流社会指什么呢?
陆:就是说有关三峡的很多问题,比如泥沙、水土保持、防洪效益、生态等话题,都要在三峡工程的伟大意义这样一个背景上来看,不是不能提三峡工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要在肯定三峡工程意义的前提下来认真解决问题。三峡工程不是百无一失,但应该有一个态度,就像汪恕诚部长今天在船闸验收仪式上讲的,要尽量减少不利的一面,增加有利的一面。拿一两个问题就否定三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不理性的态度。
新京报:作为一个事关全民族的重大话题,在三峡工程的争论上,有人确实容易表现出一种冲动的情绪。
陆:三峡工程不是一个感性的工程,而是一个理性的系统工程,是时间、历史和人的智慧的共同结果,我们肯定它的伟大意义,也不是一种感情的维护,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排沙量有望进一步提高
新京报:正如您刚才所说,在一种主流眼光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更全面客观地谈论三峡工程的成就以及那些为人关注的问题。昨天我乘船经过三峡,看到上游的水很黄,而到巴东以后黄得没有那么厉害了。我有一种担心,这是否说明泥沙有淤积。
陆:沉淀是一种自然现象。现在正是长江汛期,也是三峡水库的排浑期,三峡工程开了8个泄洪闸,这么大的泄洪量,不用担心淤积。
新京报:三峡总公司现任负责人答记者问时,新华社记者指出目前三峡水库的排沙比为40%,也就是说有60%的泥沙留在水库里,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数据?
陆:长江水利委员会所属水文局的十几个库区水文站一年来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实测和分析,取得了大量的数据。一年来,入库的泥沙量总数是2.16亿吨,而出库的泥沙量为0.86亿吨,存在库里的是1.3亿吨。这就是说,排沙比是40%.
根据水库水下地形的实测表明,大量泥沙基本上填充了原河床的深槽部位,待深槽淤满后,排沙比会进一步提高。如果把吨位转换成体积,只有5000万立方米左右淤积在库容范围内,不会影响水库的运行。
同时,根据多年的实测资料表明,1953年-1990年宜昌站测得的泥沙量减少了27%,长江的泥沙量呈逐步递减的趋势。其中的原因是由于人类改造地貌、植树造林、植被保护以及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取得的成效,当然还要进行长期的观测分析。
新京报:有学者提出,水文站测得的常年泥沙含量数据,不足以真实地反映长江泥沙情况,因为长江大量泥沙下泄是集中在汛期,特别是洪峰到来时,携带的大量泥沙是难以准确测量的。如果说长江的含沙量逐年下降,就难以解释1998年洪水,并不算很大的洪峰流量却造成了百年一遇的洪灾。
陆:洪水的本因是泥沙淤积抬高了河床,降低了河流的行洪能力。但这是一个长年积累的后果,并不是河流当年泥沙量大了才发生洪水。洪水的来源还是降雨。
泥沙问题确实是大家关心的,当初修葛洲坝就引起过争议,说泥沙的淤积会影响到三峡的修建。事实上看来,葛洲坝运行得很好,谁也不能说它有多大的泥沙问题。
新京报:葛洲坝是低坝,三峡是高坝,葛洲坝的经验能够说明三峡的问题吗?葛洲坝有多大一个死库容?
陆:葛洲坝那么大一点库容,都没有问题,三峡的泥沙淤积眼下就更不用担心了。
谈论重庆淤港为时过早
新京报:长江含沙量下降,江水变清,是否会引起上海被海水淘刷的危险?
陆:长江总的泥沙量有限,对入海口淘刷有限,也许崇明岛的淤积扩大速度会减缓。
长江、三峡水库与埃及尼罗河阿斯旺水库性质完全不同,尼罗河是多泥沙河流,而阿斯旺水库是一个多年调节的水库,大量泥沙淤在库内,清水对入海口淘刷较为严重,海岸线有后退现象。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去实地观察过,经过一定的护岸整治,这一现象已被遏止,海岸线是稳定的。不用担心长江入海口,当然也要加强监测,如有坍塌现象,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是可以解决的。
新京报:上海担心的是江水变清,重庆的担心却相反。如果说坝前的淤积有死库容保着,那库区上游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呢?
陆:坝前的泥沙淤积其实没有必要担心,到达坝前的泥沙颗粒已经很小了。泥沙的问题是在上游,在库尾。其实,和水体会翘尾巴一样,泥沙淤积也有一个翘尾巴的问题,库尾和坝前的淤积不是水平的。我们又在金沙江上修水坝,大量的泥沙又拦在上游了,加上水土治理,三峡是肯定不会像有些人所说变成第二个三门峡的。
新京报:前一段有媒体报道了重庆方面对泥沙的担心,最主要的是重庆九龙坡港和朝天门港可能会淤积,文章还提到三峡总公司每年出几亿元帮重庆人清理淤沙。
陆:重庆的淤积主要是砂石,一年通过重庆寸滩的砂石量是5万吨,算体积是2万立方米,相对于三峡总库容来说是个不大的数字。当然,也要认真解决。现在嘉陵江上也已修了几个大坝,来的砂石量减少了。重庆港的淤积可以疏浚,任何一个港口都有疏浚的问题。如果影响了重庆的航道,三峡总公司肯定会出钱,但现在没这个现象,还早得很。
在三峡工程论证中,重庆港的淤积以及疏浚措施都是考虑了的。其实,三峡水库上世纪80年代的设想是水位150米,为什么最终定在175米?就是因为重庆提出来要修就修到175米,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港。
新京报: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重庆人对泥沙淤积的担心也可以理解。
陆:我到重庆的港口看过,九龙坡港设备落后,装卸货转运很麻烦,不是一个现代化的港口。朝天门也无非是客运。重庆自己也有一个设想,要在寸滩另建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码头。但这是它自身建设的事情。还有沿江城镇包括重庆另辟引用水源的问题,也是它自己的需要,不能以这个理由来要钱。
新京报:眼下库区能得到的补偿主要是哪些?除了上次说的三峡电站每一度电里抽4厘钱扶持库区移民后期建设,还有其他的吗?
陆:以前重庆提出不要三峡的电,现在它又提出要三峡电,我们经过协调也同意向它送电。三峡发电交纳的增值税中,84.67%归重庆,只有一小部分归湖北。蓄水到175米后,一年发847亿度电,一度电二毛五,增值税的交纳比率是7%或者8%,可以算出重庆一年得到多少钱。三峡总公司在移民补偿方面也超出原计划很多,新的土地法实施后,公司增加了35亿元资金作为对库区的补偿。
新京报:我在库区了解到,以前一段时间大手大脚,现在忽然没钱了,一些县市的政府部门非常不习惯。这是否会引发新的要钱冲动。
陆:库区城市规划得太大,一些地方的新城超出老城多少倍,搞那么大,只有那么些人,“产业空心化”不就是这么出现的吗?我不同意“产业空心化”这个说法,是它自己只有那么大一点盘子!“要想富,下水库”,早就下了封库令,不准再在库区水位线下增加人口。现在一些地方纷纷叫嚷移民数要增加,113万包不住,竟然还有说要超过200万的,这些论调都有,无非还是要钱。不经过调查核实,是不能由他们说了算的。
新京报:其中是否确有水体“翘尾巴”效应超过估计带来的移民增加?重庆库尾地区地势平缓,稍微的水体高度增加就会带来大面积的移民增加。
陆:现在蓄水只到135米,离重庆还远,谈不上翘尾湖北宜昌报道巴的问题。翘尾巴的计算也很复杂,光靠模型也不行,也要实际调查。
发电防洪不矛盾
新京报:三峡库区的水位原已达到139米,现在为何又降到135米?
陆:现在是长江汛期,国务院指示我们降到135米,留下4米的库容,还可以调节一点洪水。这就体现了三峡工程第一位的效益是防洪。
新京报:三峡工程的排沙模式是蓄清排浑,在汛期要加大泄洪量,降低水位。从防洪考虑,汛期也应该留出更多库容。但低水位又不利于发电,作为一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企业,三峡总公司如何平衡防洪和发电的关系?有媒体报道,175米对于三峡总公司来说是一个诱惑。三峡的工期也确实提前了。
陆:三峡工程最终完工后,枯水期水位保持在175米,汛期则降到145米,留下221亿立方米库容,以保证防洪要求。发电量取决于势能高度和水量,枯水期水位高,但水量小;汛期水量足,水位又低。三峡电站全年发电847亿度,是已经考虑了汛期降低水位的因素的。
计算下来,三峡全部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转的发电时间为每年4600小时,而其他电站包括核电站一年的发电时间也不过4000—5000小时,所以三峡装机容量的利用率并不低。再说,作为一个企业,当然要追求效益最大化,但我们是国有企业,首先考虑的是社会效益。可以说,防洪和发电效益二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
新京报:有报道提到,三峡下游近期在全面加固堤防,目的是确保三峡电站能够正常发电。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三峡的发电还要靠下游的加固堤防来保障吗?
陆:最近下游堤防检查中又发现了豆腐渣工程。加固堤防当然是必要的,荆江大堤本身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堤防。这和三峡的发电没有任何关系。
库区航运大为改观
新京报:三峡的效益中还有航运。今天又正好是船闸通过国家级验收的日子。我了解到船只目前通过船闸的时间超出设计时间两个半小时,达到4个钟头。
陆:目前船只过闸的时间确实有3个半到4个钟头,客轮要短一些,货轮长些。其实主要是等待过闸的时间长,要编组,每一艘船进闸后要固定住,再让下一只船入闸,这个等待的时间就相当长。船闸只运行了一年,以后随着操作的成熟,过闸的时间会越来越短,现在一天过闸次数是27次,以后有加一倍的可能。再说我们还有翻坝机,客轮可以使用,那个时间只要半个钟头。现在上下游没有船只积压,说明三峡水库没有碍航。
新京报:现在水位只有135米,以后蓄水到175米,过闸的时间要求会不会更长?
陆:水位高低和过闸时间长短没有直接关系。三峡船闸是五级船闸,眼下由于水位低,只用了四级,以后用到五级,要多一些时间。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船舶缺乏一个规范,大的小的都有,不好编组进闸。船舶进行改造,需要一个过程。我参观莱茵河,它的过闸效率很高,船只都像火车一样,可以一节节连起来的。但它用了40年的时间使船舶规范化。
新京报:过闸是对航运的一种限制,但库区的航运确实比以前畅通了。
陆:从坝前到重庆,航道大大改观,出现了“黄金水道”局面,以前晚上有的航段不大敢走,现在都没有问题了。虽然付出了一点过闸时间,整体说来对航运是有大利的。倒是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很多货运汽车不走公路,搭运滚装船运输,它本身的重量是个无效运量,加上超载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以后随着上游码头的装卸规范化会得到解决。我们现在不准它过闸,要它走陆路翻坝再装船。
没有永远静止的生态平衡
新京报:目前三峡库区水体多少天能够全部更新一次?
陆:眼下三峡库区水位是135米,库容是123亿立方米。通过三峡大坝的年流量是45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下来,一年可以更新几十次。蓄水到175米时,水库库容是393亿立方米,与年流量4500亿立方米相除,也可更新10多次,并不是一潭死水。通过防污措施的落实和人们素质的提高,三峡水质的污染是可控的,目前水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倒是一些人的素质存在问题,好多船只到港,垃圾不是转到岸上,而是往水里一扔。
新京报:确实,水库不少地方还有大量漂浮物。
陆:三峡工程是改善生态,不是破坏生态。生态平衡是相对的,人口的增长本来就会引起生态不平衡,要靠工程和非工程手段来改善它。假如无人要用水,就不需修水库;假如洪水淹不到这么多的人,也不需要修大坝。什么是洪水?就是人和水争夺陆地面积。这是自然规律。修水库淹了土地,但下游保证了良田,用坏的地换好的地,少的地换多的地。没有永远静止的生态平衡。
“三江并流”我无法评价
新京报:最近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中国召开会议,对包括三江并流在内的中国7处自然、文化遗产亮了黄牌,你对这件事有何评价?
陆: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二者不一样,文化遗产当然需要保护,自然遗产,比如一些地质公园,可以供人类研究远古的地质,也应该保留。“三江并流” 这个自然遗产,说实话我无法评价。景观也是为了人看的。有人在那里生存,就在不断改变。改变一点自然状态,对可持续发展来说有好处。修一个坝,对整个大地来说是很少的一点,人的力量有限,对于大自然来说很微小。究竟有多大影响,发生什么变化,要分析。如果确实有大的破坏,则不能建。
新京报: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警告会实际影响怒江以至金沙江的水电梯级开发计划吗?
陆:国家不会一刀切地说怒江不能开发,也不会说哪儿都可以建坝。现在怒江尚未动土兴建,但也不是搁置。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头脑清醒。
新京报:与三峡水库蓄水一年的周期大致同时,在洞庭湖等地段爆发了大规模的血吸虫病。查阅相关资料,阿斯旺等大坝修建之后,也带来了血吸虫病的泛滥。最近库区万州市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提出,蓄水后库区条件变化,利于血吸虫生存,要加强这方面的预防,防止下游的血吸虫病原通过船舶、人体等带到上游。三峡蓄水和血吸虫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联?
陆:三峡即使不蓄水,恐怕上游也会有这个问题,加强措施预防血吸虫病是必要的。
一味反坝有非理性情绪
新京报:《十问三峡》中提到了世界大坝委员会关于水坝利弊的调查报告。现在看来,这个委员会是由曾资助许多大坝建设的世界银行和世界发展委员会联合组织的,是一个中立的组织。
陆:我很清楚这个委员会的背景。委员会吸收了大量反对建坝的人士,成立后,曾提出要在2、3年内拿出一个大坝的规范,我曾当面对他们表示这不合适,各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情况来确定。
新京报:“炸坝时代”的提法也许是有问题的,但是不是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关于大坝的争议时代。
陆:美国和中国都有7、8万座大坝。个别大坝的争议是有的,一概而论的反坝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主要是自然保护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人做任何一件改变自然的事情都是不行的。当然他们有很多做得对的事,但他反对建任何的坝,这个就错了,里面带有感情色彩和非理性情绪。(新京报记者袁凌湖北宜昌报道)